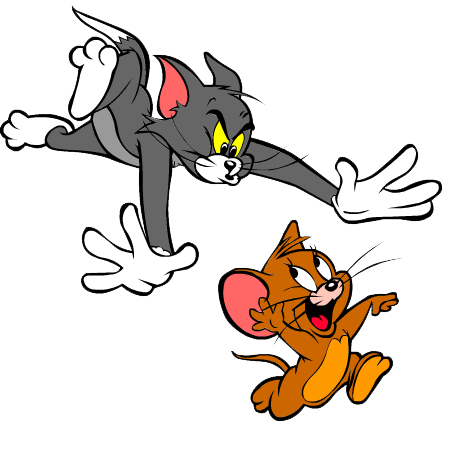新新默存|英雄迟暮宋先科
1.
3月14日一大早,我坐上G1321次高铁,列车经过南昌、萍乡、长沙、娄底等沿线城市,六个多小时之后到达溆浦南站。
这是我第一次来湘西,出站之后发现,从高铁站到溆浦县城还有四十多公里山路,并且外面居然没有出租车候客区。
三五个穿着深色衣服的黝黑汉子围上来,问我要去哪里,我对搭黑车心里有点抵触,有些犹豫,好在不远处停靠了几辆中巴车,是连接高铁站和县城的班车。
我走过去上了车,十多分钟后中巴车基本坐满,司机说了几句我听不太懂的话,车子就启动了,晃晃荡荡地在盘山公路上绕行,路边各种树木都已绿意盎然,而绵延不绝的油菜花令人有梦幻之感。
大约一个半小时后终于到达溆浦镇南医院,我找到宋先科病床,看他躺靠在病床上,身体瘦削,脸有点肿,露在外面的脚部有明显瘀血,局部有些溃烂,我问老宋,情况如何?
宋先科回答说这两天情况还可以,然后下午晚点还有两个同学从怀化赶过来,让我和他们见见。
老宋说话口音重,语速快,多年不见,我发现更不容易听清楚,一来二去,不知怎么他已经在和我说经济萧条和俄乌战争,我不得不把话题拉回到病情,才知道早在2013年,他就查出有了糖尿病, 2017年又摔了一跤,这些年身体状况都不是很好。
后来还是他弟弟把我拉到一边,说宋先科因为糖尿病并发症病情恶化,春节前住院一直到现在,前几天他因为急性心衰进行抢救,医院发了病危通知书,好在抢救过来了,目前算暂时脱离危险期。
在抢救过程中,宋先科对他弟弟提到了我以及另外几位朋友的名字,因此他弟弟通过宋先科微信给我发了消息。
我应该有六七年没和宋先科见面了,我的大部分朋友应该也不知道宋先科。
不过多年以前有一句很著名的广告词:“世界看中国,中国有先科”。
当时,王俊秀等朋友就拿“中国看先科” 来揶揄老宋,希望他能干点轰轰烈烈的事。
多年之后,先科电器早已没落,而六十挂零的宋先科豪情不减,但出师未捷,身体已经虚弱不堪,要站起来都已经很不容易。
我站在他病床前,心绪翻滚,不知从何图说起。
2.
宋先科和我大概是2002年前后通过天涯社区认识。
关于天涯社区的起起落落,最近有很多动静,商业上,天涯社区应该很难起死回生,但那个年代,天涯社区毫无疑问是最火热的时政论坛,影响了无数的热血青年。我早年和许多朋友相识,都是源自天涯社区。
初识宋先科,感觉他不修边幅,嗓门很大,说话直来直去,也不太顾及场景,有时候难免让人觉得尴尬。
当然这种粗犷只是一个浅层表象,宋先科并非一个大老粗,他1990年考上北大硕士,追随法学名宿龚祥瑞先生研习法律,和当年很多北大风云人物有过来往。
他有个同学,也和我很熟悉,那就是同样来自湖南的杨支柱。
杨支柱在青年政治学院任教期间,创办了学而思网站,是本世纪初非常有名的学术和思想网站,而杨本人更是网络论坛上一支健笔,经常以尖锐文字针砭时弊,因此被学校当局忌恨,后来被剥夺教职,贬到学校图书馆工作。
杨支柱后来专注于计划生育议题,为生育自主鼓与呼,成为这个领域的权威声音之一。
宋先科说起那些年在北大的经历,如数家珍,会有些许作为北大人“与有荣焉”的那种得意。
宋先科一直念念不忘龚祥瑞对他的影响。
龚祥瑞是钱端升门下三杰之一,40年代公派留学英国,回国后命运多舛,历经各项政治运动,后来在北大任教,言传身教,桃李满天下,当代很多重要法学和政界人士都出在他门下,其中就包括……龚祥瑞逝世后,宋先科也写了悼念文章。
宋先科记忆力超强,他会大段大段地背诵卡莱尔的《英雄和英雄崇拜》或者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的经典论述,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一个激情燃烧的知识人模样。
可以想见,那些求学和教育经历是如何影响了他后来的人生选择。
宋先科北大硕士毕业后,被分配到湖南某地司法局,不过他很快因为参与当年的一些民间活动(本文显然不便展开),而身陷囹圄。
多年之后,我问他,在里面感受如何,他回答了一句:那不是人过的生活。
不过由于这段经历,在和人交往的时候,老宋的警惕性就很高,甚至有点神经过敏,有数个场合,我注意到,在交流几句话之后,老宋会借口有事提前离开,事后他和我说,某某某很可能身份特殊,不可信任。
老宋这些疑神疑鬼的反应,也影响了一些朋友对他的观感和评价。
我有时候也会想,一个人在非人的地方熬过两年之后,多少会遗留下很多心理创伤,对于一些人和事,会过分敏感,其实也难以避免。
3.
从里面出来之后,宋先科自觉在湖南呆不下去,而他很多校友都在广东发展,大约在1996年前后,宋先科到了深圳,他先是做律师,(这次在溆浦他病床边,我才知道老宋1988年就考出了律师资格),但他的律师生涯显然并不成功。
宋先科成天思考宏大话题,对法律条文似乎缺乏钻研的兴趣,他和人打交道时候缺乏回旋能力,他更不会和官府勾兑,综合这些因素,显然很难帮客户打赢官司。
我曾经听他谈过一些案子,他认为他的身份限制了他发挥的空间,当然宋先科对法律本身缺乏信心,他认为法律并没有什么作用。
宋先科后来转战广州,因为在广州,他似乎能找到更多的朋友,尤其是当时在媒体圈里叱咤风云的诸多北大校友,那种融入其中的兴奋感对他来说,有重要的精神价值。
印象中,宋先科曾经用苍凉笔调写过一文章《广州火车站》,描绘那个年代广州火车站的混乱无序,刻画出社会底层的困顿画像。
这篇文章曾经在天涯社区反复转发,不过如今我却怎么都搜索不到这篇文章。
宋先科做过的最高光的一件事,或许是推动广东人文学会的成立。
2003年,孙志刚事件引发舆论哗然,在强大舆论压力之下,官方废除了收容遣送制度,所谓XX新政说法不胫而走。
在广州蛰伏许久的宋先科,似乎也嗅到了变化的契机,那一阵子他和一些志趣相投的朋友东奔西走,寻求做事的契机。
在广东政界元老们加持之下,一个名叫广东人文学会的社团正式成立,这个机构网罗了广州学界精英,其中包括袁伟时、林贤治等知名学者,还有一些企业家也慷慨捐款,任 仲 夷,吴 南 生 ,前中宣部部长朱 厚 泽等老人挂名顾问。
广东人文学会的成立,得益于当时比较宽松的大环境以及民间社会的热情,宋先科具体如何运作,我不得而知,但在促成学会成立过程中,他无疑是重要推手之一。
等广东人文学会真正挂牌之际,宋先科在其中的职务是众多副秘书长之一。
我记得有一次他和我聊天,他说为了安慰家里老人,电话里告诉他们他在广州混得不错,在一个省级单位任职,相当于副厅级待遇。
我不知道老宋有没有成功蒙蔽家里人,反正他这次高光时刻只是昙花一现。
广东人文学会高调宣布成立之后,真正想做事自然面临各种障碍,老宋过往经历使得他不得不淡出这个机构。
后来,广东人文学会虽然也举办过一些人文活动,但活动基调大抵不痛不痒,没有引发波澜。多少有些讽刺的是,广东人文学会存续至今,但早已没人把它当回事。
多年之后回望,当年网络上各种喧嚣都已沉寂,但将来的历史学家或许会注意到那些历史时刻曾经掀起的小小波澜。
4.
虽然个性差异不小,2010年前,我和宋先科还是有相当多互动。
我记得有一次他来杭州,我给他安排在青芝坞附近的酒店,我听他聊各种江湖轶事一直到深夜,那天我就没回家,干脆和他在同一个房间住下。
第二天凌晨5点多,他一骨碌坐起来,又接续前一天晚上的话题,一个人侃侃而谈,他具体说了什么,我已然记不清,但肯定都是各种宏大话题。
我几乎是在睡梦中被他吵醒的,根本不想接茬,就和他说,老宋,我们晚点再说!
那时候的宋先科,心气十足,有一种莫名的紧迫感,做梦都想干一番大事。
宋先科还是做了不少尝试,但现实是,做什么都容易碰壁。
2006年,宋先科得到了他北大校友、暨南大学庄礼伟教授和另外一个朋友的支持,成为“社会责任国际”的研究人员。
那时候企业社会责任还是一个热门话题,有很多国际机构都关注劳工权益问题。
宋先科在东莞租了一个房子,准备收集资料,评估当地大量制造企业的工人待遇和权益问题。
(2018年12月,庄礼伟教授在泰国进行学术研究期间,不幸车祸离世,宋先科撰写了纪念文章,《稻草与飞花》这个公号曾经转载。)
宋先科大概在东莞呆了一年多,我并没有跟进了解他为“社会责任国际”所做的工作成果,但在他多次力邀之下,我的确去东莞看过他,具体和他谈了什么已经完全没有印象,但在东莞东江游泳的经历却很难忘记。
宋先科租的房子离东江很近,每天在东江游泳成了他锻炼的方式,那天下午他陪我去东江游泳。
那一段江面大概300-400米宽,老宋游到江中央,就往回游了。
我当时自觉体力还可以,或许也有点逞能的心态,因此继续往前游,快游到对岸的时候才折返,没想到上游忽然放水,等我返程时候,水流加速,根本无法直线折返,身体不断被水流往下带,硬是被带成一个长长的斜线,加上要避开江面漂浮的水草和杂物,游起来相当吃力
到最后一段距离,我感觉体力消耗殆尽,只能仰浮在水面上,不时蹬腿形成一点推力,等真正返回岸边,已经和出发点相差甚远。那大概是我这辈子距离被淹死最近的时刻。
宋先科经常把他的朋友介绍我认识,有一次,我路过武汉,住在汉口火车站附近,他非让他在华中科技大学的同学请我吃饭,我打车去校园,和他同学匆匆见了半个小时,但打车来回路上花了2个多小时。
另外一次,在宋先科推荐之下,杜钢建教授来杭州时约我吃了一顿饭。
宋先科和杨支柱对杜钢建评价都颇高,因为在90年代的患难岁月,他们一度在杜钢建家里住了个把月。
印象中,那天杜教授十分健谈,对未来也有很多想法,他谈到要推动建立一个天目山书院,依托浙江民间资源,做一些民间独立学术研究,这件事后来无疾而终。
后来杜钢建教授转到湖南大学任教,提出英国人起源于大湘西等雷人观点,因此声动江湖。不过宋先科一直认为,这些是杜钢建教授故意恶搞的一种另类表达。
大概在2011年,宋先科和许民权相约来杭州和我会面,不过那阵子,我正试图重新定位生活轨道,对许民权醉心的一些表达方式,缺乏热情。
许民权成为了时代的孤勇者,而宋先科则继续他磕磕碰碰的人生轨迹。
宋先科最后一次来杭州,大约是2017年,我对他的满脑子想法也有些意兴阑珊,陪他在西湖边转了转,没留下其他什么记忆。
5.
多年的边缘人生活,经济上的困顿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不过有很多次,宋先科都曾经尝试解决财务问题。
我记得他最早的一次生意努力,是卖酒。他和一个朋友盘了江西一个老酒厂的几吨白酒,他请了他北大校友范美忠作代言人—肯定没给啥代言费,也叫我帮忙吆喝。
我不懂酒,更不懂卖酒,他说卖酒的事情我就没上心,不过我的确从他那买了一箱酒,老宋买一送一,那些酒我也作为顺手人情,转送给了几个朋友。
有朋友说酒不错,有朋友说酒很难喝,不过不管怎样,宋先科卖酒事业后来也无疾而终了。
有段时间,宋先科认识了一个包工头,他们就合伙试图参与承包某段铁路的土方工程,宋先科打电话问我有啥资源,我给他浇了一盆冷水。
又有一次,宋先科试图在怀化承包一片林地,说那里有很多珍贵林木,包括红豆杉17000株,银杏3000株,这些事,他都发过资料给我,我翻看微信记录,我的回复简直有些伤人,我说你不是做生意的人,不要浪费时间了。
对我的直言不讳,宋先科倒是不以为意。多次尝试失败之后,宋先科有一次他给我发来一句话:生意不做了,一生只做一件事。
我从来没问过宋先科的感情生活,印象中,他倒是和我提到过,在深圳和东莞的时期,都有近乎对他崇拜的女生,不过老宋从来没有带女朋友出场,他也没有结过婚,至今孑然一身,他病重住院期间,是他弟弟承担着主要的照护工作。
他弟弟和我说,春节都是在医院过的。
我顺便问了他弟弟一句,这些年宋先科的医疗费用怎么解决的?他说老宋办了当地医保,医药费部分能报销60%左右,主要负担是护理费用和其他杂费,家里的确已经捉襟见肘。
有时候我难免会想,在一个正常时代,在一个正常社会,宋先科这样的人会怎样生活?
以他的个性,他不可能在体制内做一个安分的公务员,他大概也满足于做象牙塔内的一个知识分子,以他不关注细节的风格,他未必能成为一个好律师……
以他对政治事务的热心,或许他可以成为地方议员,从事他经常挂在嘴上的“以政治为业”。
但我怀疑他能否成为一个合格的政治人物,他内心那种激情涌动的梦想,会造就一个高傲的自我,注定和现实很难兼容,成为失意者,几乎是某种宿命。
当然,失意是多种多样的,在一个正常社会的失意,可能是心甘情愿的,而在一个不正常社会的失意,则注定抱憾终身。
当然,失意不等于失败,起码宋先科并不认为自己是失败的,我印象中,他从来没有怨天尤人,从来没有哀叹命运的安排。
看着躺在病床上的宋先科,我想到了身患癌症的杜导斌,想起了和我们争论不休的笑蜀,我的脑海里出现了许许多多的旧人旧事,我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是的,我们这些20来年前相识的朋友,有些人已经老去,有些人则病怏怏,不少人选择了飘零海外,大部分都不再年轻,历史车轮已经把一代人碾压成泥。
而深藏于我们内心深处的那些信念和价值观,却依旧鲜活热烈,拒绝被历史埋葬,现实和信念的这种撕裂感,让人不胜唏嘘。
6.
在认识宋先科之前,我并不知道湖南溆浦这个地方,他曾经多次邀请我去溆浦玩一玩,我多次答应他,但从来没认真计划过。
这次终于来到溆浦,宋先科早年的学生海洋律师驱车带我在县城兜了一圈,县城看起来经济不甚发达,当地没有什么特色工业,主要靠外出务工人员的务工收入。
我回想起宋先科不止一次和我讲过,溆浦有多少人在广州和深圳打工,尤其是出租车司机中,很多都是溆浦人。
有一段时间,我知道他认真在出租车司机当中发展溆浦老乡,经常和他们打成一片,但他一直没有等到利用溆浦出租车司机闹罢工的机会。
群山环绕的溆浦,也有其独特的文脉源流。据称当年屈原在流放途中,曾经在溆浦居住数年。溆浦之名,取自屈原诗歌《涉江》,“ 入溆浦余儃徊兮,迷不知吾所如”。
而近代历史上,溆浦出了一个向警予,是中共早年革命家,也是女权运动的先驱之一。
很难从宋先科身上看到和屈原相似的印迹。不过海洋律师和我说,他认为宋先科和向警予有些神似,都是理想主义者,都有革命家气质。
向警予纪念馆是当地主要的旅游景点,而宋先科所坚持的那些理念,似乎看不到任何机会。
值得欣慰的是,宋先科的努力并非完全不落痕迹,海洋律师认为,是宋先科帮助他走出了原来的那些观念桎梏,因此他对宋尊敬有加,忙前忙后,付出了很多心力。
宋先科的老家离县城大概十来公里,他父亲是村干部,但老宋告诉我,饥饿是童年唯一的记忆。我想起最近看到一篇文章《糖尿病与大饥荒》,其中提到:大饥荒改变了居民的生活习惯,使他们即使在食物丰沛的时期仍然习惯于摄入高热量食物,诱发了糖尿病的高发。
对特定疾病的医学溯源,在科学上是有意义的,但对经常在病床上昏迷的宋先科,显然已经没有意义。
那天傍晚临走之前,我见到了宋先科早年的几个同学,他们力邀我多留些时间,晚上和我好好喝一杯。
和他们聊天得知,宋先科1980年毕业于怀化师专,毕业后曾经在一个中学教化学,考取了北大研究生之后,命运彻底改变。
而他的同学们则在官僚体制内混了多年,也都到了退休的年龄,对形势走向,大家似乎有一种不需言明的默契,而对宋先科,他们则不吝赞许,对他的记忆力更是折服。
宋先科在病床上接话说,他还能大段大段背诵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 ,以及雨果的“悲惨世界”…..
由于我自己老母亲病重,我必须及早赶回去,当天晚上我就得离开溆浦。
和老宋作别,我眼里有泪水,但我并不悲伤,命运虽然残酷,但一定程度上,这些都是我们自己找的。
老宋,好好养病,再见。
2024年3月15日草稿,3月23日改定。
赞(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