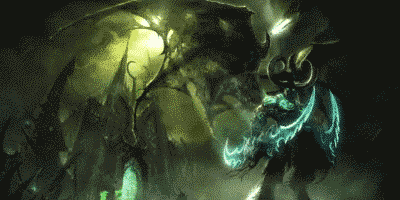北青深一度|清北商科毕业生“疯狂赚钱”的野心落空后|深度报道
过去十多年间,清华、北大等顶尖高校的经管、金融类专业吸引了一批“最聪明、最能干、最勤奋、最有学习能力的人”,他们满怀野心,相信未来充满可能性——进投行,年入百万,和企业高管谈笑风生,过上“空中飞人”般忙碌但光鲜的生活。
2023年9月,以为“形势一片大好”的他们迎面撞上剧烈收缩的招聘市场,之前在职业规划中从未出现过的银行变为“救命稻草”。
从投行到银行,他们做出职业选择改变的同时,也意味着进入截然不同的另一套评价体系——“都是人情那一套,一眼望得到头”。
这背后是金融业近两三年所经历的震荡。
盛时,“大家都疯狂挣钱,也预期以后会疯狂挣钱”。
监管来得猝不及防,从2022年5月开始,几道“限薪令”,一纸“827新政”,以年终奖和福利补贴的缩水为开端,投行的降薪、裁员、缩招接踵而至。
从投行到银行,走上一条更安稳但同时也更封闭的轨道,他们中有人心怀不甘,仍期待有朝一日能跳出。
也有的人主动让渡工作带来的物质回报和成长,转向对更加稳定和丰富的个人生活的追求。
这是一个关于信心和预期的故事,发生在金融业,不止于金融业。
“最聪明的人”
今年春节,徐凯陪母亲到家附近的银行网点办卡。
营业员看起来和他年龄相仿,穿一身老式西装,头也不抬地给他们讲解办卡的手续,语气不带起伏,一套冗长的流程不知反复说过多少遍。
隔壁柜台,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将手机屏幕贴到玻璃上,拉高声音问对面,“小伙子,这个理财APP怎么用啊?”
徐凯对母亲自嘲,“这就是我以后的生活。”
即将从清华大学经管类专业硕士毕业的他从未这样预期过自己的未来,直至与残酷的就业形势交手。
去年9月底的一天,他在“三中一华”(指国内四家顶级券商,包括中信证券、中信建投证券、中金公司以及华泰联合证券)之一的暑期实习即将结束。
晚上6点,他合上电脑,走出北京金融街附近的一座高楼,辗转1个小时后回到10多公里外的宿舍,掏出电脑正打算继续加班。
“叮”,一封新邮件传来,他点开,加粗的一行字冲入眼帘:我们很遗憾地通知,您未能进入XX证券的录用环节。
瞬间,“心拔凉拔凉的”,按照往年的留用率,他本以为自己稳操胜券。
徐凯只得投入茫茫秋招大军,经过几个月的提心吊胆,终于在今年初收到了国内一家银行总行管培生项目的录用通知。
签三方协议书前,他有些犹豫,想等等更好的机会。
同学劝他,“现在这个行情下,别要求太高。”
他不曾想到会有这样一天。在过去十多年间,经济、管理、金融是最受追捧的专业类别之一,吸引了大量的优质生源。
清华、北大等顶尖高校的商科生更是“金字塔塔尖”般的存在。
曾任清华副校长的著名生物学家施一公在2016年的一个演讲中感慨,“清华70%至80%的高考状元去哪儿了?
去了经济管理学院。连我最好的学生,我最想培养的学生都告诉我说,老板我想去金融公司。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高西庆也曾公开表示,“
今天世界上的金融机构吸引了整个社会上最聪明、最能干、最勤奋、最有学习能力的人。”
在各类金融机构中,投资银行(在国内常被称作“券商投行部”)因其高薪和光鲜尤其令商科生们趋之若鹜,“可以说是皇冠上的明珠”,一位清华大学金融学专业的学生这样形容。
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就业质量报告中,投行常年位列就业去向首位:2019年,24.3%的本科生和39.5%的金融硕士毕业后进入投资银行;2020年,17.8%的本科生和25.4%的金融硕士毕业生入职投资银行。
一位北京大学金融学专业的大四学生记得,四年前入学时,学院做过一个关于 Target Company(目标公司)的调查,“高盛、摩根士丹利、中金、中信”是大部分同学的答案——都是投行。
这背后是一条不言自明的“鄙视链”:最顶端的是投行,银行排在末尾。
每个人的目光都朝上,没人愿意低头。
但今时不同往昔,“现在这个行情”意味着他们必须接受几年前“压根不会考虑”的工作。徐凯出身于一个“银行世家”,他的母亲、舅舅、姥爷都是银行工作者。
母亲之前经常苦口婆心地劝他:“儿子,银行总行可好了,待遇好,风光。
每次总行管培到分行学习,行长都得陪着。”母亲说的次数多了,他急了,“我去什么银行?”
现实的当头一棒来得突然。首先到来的是远低于往年的暑期实习留用率,许多优质岗位往往在这一环节被锁定。
多位清北商科生告诉深一度,2020、2021年,投行暑期实习留用率可以达到50%,到了2023年,平均留用率只有25%左右。
紧接着是秋招时明显的缩招。
很多投行的招聘计划只有个位数,有的“干脆不招”。
招聘人数和待遇同样稳定的银行在这时变成清北商科生们的“救命稻草”,“四大行”(指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尤其受到青睐。
一位在“四大行”之一工作的亲戚曾向徐凯透露,2023年,他所在银行的管培生岗位在全国招大约60人,而应聘者中有将近3000人的简历包含北京大学或清华大学的求学背景。
这在往年是不可想象的。
徐凯记得,在2023年9月前,他和同学对工作的讨论中甚至从未出现过银行这个选项。
竞争骤然加剧之下,招聘市场供需双方的主动权极大地被逆转。“海投”成为普遍策略。
秋招期间,徐凯一共投递了三四百个岗位,最后只收到了三个offer,“之前准备了那么久,付出了那么多,辛辛苦苦地卷出来,最后被当成大白菜,被原先看不上的公司挑挑拣拣。”
“很无力,很不甘心。”他强调,“这是大家一致的感觉。”
徐凯经常在银行的面试现场偶遇同专业同学。第一次觉得巧,第二次觉得挺有缘,到第三次甚至更多次之后,大家相视一笑,笑中尽是苦涩。
市场曲线
金融业曾“高歌猛进”。
中国政府网每年发布的金融市场运行情况报告,勾勒出市场变化的曲线。
2020年的报告中,“增长”“上涨”等类似表述贯穿始终——债券市场发行规模显著增长,现券交易量增加,收益率曲线平坦化上行,市场投资者结构进一步多元化;货币市场利率显著下行,银行间货币市场交易量增加;利率衍生品成交量同比上升,互换及期货价格小幅下降;股票市场主要股指大幅上涨,两市成交金额显著增加。
在中金公司投行部员工王安琪的记忆中,那是“一波大年”,“大家都疯狂挣钱,也预期以后会疯狂挣钱。”
2021年,市场整体保持增长态势。
徐凯就是在这样的一年考入清华,那时他们同学间开玩笑时会说,“中金不是有手就能去吗?”
这并非夸张,王安琪记得,那是公司疯狂扩招的两年,“几百几百地招”。
2022年,嗅觉敏锐的人开始注意到行业下行的征兆。
最显性的变化是几份金融业“限薪令”的陆续出台,旨在控制薪酬差距——
5月,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证券公司建立稳健薪酬制度指引》;6月,中国基金业协会发布《基金管理公司绩效考核与薪酬管理指引》;8月,财政部金融司发布《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国有金融企业财务管理的通知》,要求金融企业高管及重要岗位员工基本薪酬一般不高于薪酬总额的35%,绩效薪酬的40%以上应当采取延期支付方式,延期支付期限一般不少于3年。
当年的金融市场运行情况报告中,措辞变得谨慎:债券市场平稳运行,国债收益率涨跌互现;债券市场高水平对外开放平稳有序,投资者结构进一步多元化;货币市场交易量持续增加,银行间衍生品市场成交量保持平稳;股票市场主要股指回落。
在王安琪和谢超公司的茶水间、卫生间、楼梯间,一些小道消息流传——风雨欲来。
2023年对于金融从业者来说是不平静的一年。
他们首先迎来的是大幅缩水的年终奖。
谢超在一家业内排名前十的券商投行部工作,按照往年惯例,年终奖一般是9-12个月的工资,但2023年只发了2个月的额度,“象征性地发一发。”王安琪听说,有同事收到年终奖后吐槽,“比上一年年终奖缴的税都少。”
日常的福利和补贴也在减少。在王安琪的公司,差旅标准骤降,原来酒店可以住一晚三千的万豪,现在只能在如家和汉庭之间选择;谢超公司原来的餐标是一天100元,“多花点也无所谓”,现在则要求严格控制在标准内,且必须在公司附近消费。
2023年8月27日,对投行从业者来说是历史性的一天。
证监会发布《证监会统筹一二级市场平衡优化IPO、再融资监管安排》,明确提出“合理把握IPO、再融资节奏”“阶段性收紧IPO节奏”。在业内,这道文件也被称作“827新政”。
IPO,意为“首次公开募股”,是企业上市的必经之路。
在A股全面实行注册制的当下,企业在提交IPO申请后、成功发行上市前,需要依次经过受理、审核问询、上市委审议、报送证监会、证监会注册几个环节。
监管收紧之下,很多企业的上市之路走得磕磕绊绊。“827新政”推行后,IPO的受理数量明显减少,审核速度显著放缓。
2023年1月至8月,沪深市场核发IPO批文213家,启动发行193家;2023年的后四个月内,仅核发批文32家,启动发行44家。
时间回拨,2022、2021、2020年A股新上市公司分别为428、481、394家。
主动撤回IPO申请的企业也不在少数。据公开数据统计,截止4月8日,2024年已经有99家排队IPO企业撤回申请,2023年全年撤回IPO申请的企业为274家。
王安琪对记者解释,这是因为企业等不起,投资人也着急退出,“再拖拖,企业的财务业绩不一定像当前那样好。”无奈之下,企业纷纷另谋出路。
王安琪告诉深一度,“这种行政管制的妥协空间不大。”
一般来说,IPO的准备时间短则一年,长则三年,投行正是从这一过程中赚取高昂的承销保荐费用,所谓“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
但随着IPO大量终止,投行收入减少,利润下降。以一向有“投行贵族”之称的中金公司为例,据其2023年年报,投资银行业务营业收入同比减少40.3%,营业利润率同比下滑22.2%。
“利润变差,自然各种降本增效。”王安琪表示,“投行最大的成本还是人。”
降薪逐步由传闻变成现实。
目前已披露2023年年报的27家上市券商中,有12家的员工人均薪酬出现下降,降幅在2%-13%。
曾因“高薪”几度陷入争议的中金公司在2021年的人均年薪为116.42万元,2023年降为69.72万元,降幅达40%。
在这轮集体降薪中,“限薪令”针对的高层员工首当其冲。
前述27家上市券商中,22家的高管薪酬总额下降,平均降幅达15%。
《财新》在此前报道中也提到,多位接近中金公司的人士在2023年4月时曾表示,中金被股东要求削减工资包,一度传出“得砍去一半”的说法。
随之而来的便是裁员。
谢超告诉记者,“各家(投行)或多或少有裁员”,以他所在部门为例,原有70多人,2023年底开始,“主动或被动走掉了快10个人”。
据公开信息,2024年以来,中信证券的投行部门进行了人员调整,百余人从IPO股权岗转至债权融资、并购重组、投资等业务条线。
一位业内人士此前在接受《财新》采访时直言,“整个行业都是树欲静而风不止,能够转岗而非直接辞退算不错的了。
投行做项目,一个IPO团队人数少则十数人,多了得有二三十人,不同人员还可能同时跟进几个项目。
现在除了北交所和科创条线有些机会,部分从业者都是无项目可推进的状态。”
市场收缩的寒意一步步传导到招聘端。
对于就业形势的变化,身为投行内部员工的王安琪和谢超并不感到意外。
“但想不到下行的速度会如此之快,低迷的程度会如此之深。”王安琪说。
行业形势变化渗透到人才供给端存在一个时间差。大多数学生和徐凯一样,几乎是在一夕之间发现“没有地方可去”。
去年,徐凯参加过两次学院聚餐。六月时,空气中浮动着燥热,年轻人对未来的无限憧憬和野心在桌上涌动,
“大家都觉得形势一片大好”。
到了十一月,深秋,同学们交流完彼此去向后相顾无言,震动、无措、慌恐填满沉默。
两种生活
一次银行面试结束,徐凯走出大楼,一抬头,暑期实习的证券公司就在对面。
实习三个月,他从来没有留意过对面是什么公司、在里面工作的是什么样的人。
一条路的两侧,两种人生走向。
最直观的是收入上的不同,或者说差距。谢超告诉深一度记者,他所在的投行,员工入职第一年就可以拿到近百万年薪,扣完税也有六七十万。
即使面临大幅度降薪,一个月税后工资也有3万多。
至于未来的银行工作,徐凯向在其中工作的学长打听过,第一年税后月收入不到1万。
他发愁,“在北京,租房就要花掉三四千,剩下六千块够一个人活,但要是有婚恋打算的话,挺难。
”他和女友交往多年,感情稳定,但想到未来的收入,“有些恐婚”。
从本质上来说,这背后是两套截然不同的评价体系。
多位受访者表示,对于“去能力化”的担忧是他们之前很少考虑银行工作的重要原因。
春节回老家期间,姥爷、舅舅与徐凯长聊,给他普及银行内部的“文化”,打了两剂“预防针”。
“第一针”是银行工作高度流程化,追求的是合规,是风险可控,是不要出问题。
徐凯在心中默默翻译:螺丝钉一样的生活,无趣,没有新鲜感,没有挑战性。
“第二针”,银行是一个重视“人”远高于“事”的环境。
长辈们语重心长,告诉徐凯工作以后要转换思维,高度可量化的考核体系不会再有,“都是人情那一套。”
中国建设银行曾披露过一个反映各岗位竞争激烈程度的金字塔图,越靠近塔尖,岗位的报录比越高,而岗位的热度和其在体系内的受重视程度紧密挂钩。
塔尖一层的职位有董事会办公室、党委办公室、财务会计部等。
透过面试流程和选拔标准,徐凯逐渐感受到“银行体系”的特点。
在徐凯参加过的银行招聘中,一个常见的面试形式是无领导小组讨论,“考察的更多是软实力”,比如面试者的逻辑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
相较于过往的专业实习经历,候选人的学生工作经历甚至是兴趣爱好更受关注。
他还注意到,银行招聘中,面试官以男性居多,穿着一套规矩的西装,“整体气质很稳。”
“去能力化”的结果是跳出银行体系很难,“进去就出不来了”。想到未来的生活,徐凯“一眼望得到头。”
走上一条安稳但同时也更封闭的轨道,徐凯是出于无奈,也有的人是主动选择。
北京大学金融学硕士陈墨,在今年秋天将入职“四大行”之一。
此前他在一家外资投行实习过半年,对于他来说,这是一个不断认清投行的“B面”的过程。
最不堪忍受的是“毫无人性”的工作节奏。
那半年,陈墨每天8、9点起床,“干到12点闭眼,一周7天都是这样”。
除了加班,还有不计其数的出差。公司内部有一个叫做“出差率”的指标,计算方式是出差天数除以工作日总数,他所在业务组的平均出差率高达105%。
在这样的高强度工作下,“身体的变化是看得到的”。
实习半年,陈墨胖了20多斤,因为完全没时间运动,“每天凌晨回到家,简单洗洗就睡了,哪有心情运动?
第二天还要上班。”脱发,失眠,也都是他的困扰。
被迫改变的还有社交生活。
那半年,陈墨几乎在朋友圈消失,偶尔和朋友见面也都是约在公司附近,以防工作上有急事。
没有周末,没有假期,出门一定带着电脑,随时待命。
他观察身边的同事,每天都很疲惫,“眼里真的没有光”。
他记得一个入职第一年的同事。
一次,她在国外工作的男友时隔一年回国,第二天就走,她想晚上在公司旁边的饭馆和男友吃个饭。
不凑巧,那天工作特别多,同事实在走不开,一边干活儿一边反反复复按亮手机看时间,“都要哭出来了”。
到了晚上10点,工作还是没做完,陈墨看到同事出去打电话,回来时眼睛发红。
职位更高的人从工作中收获的价值感同样有限。
一位在一家顶级外资投行任总监的学长曾向陈墨坦言,工作多年,他最大的感受是虚无和悲凉,“你可以把金融市场当成一个游戏,玩赢了获得游戏币,在排名上的位置提升一些。
只能让自己沉浸在游戏里面,不敢想太多。”
“门口早餐店卖煎饼果子的大妈可能都比我有活着的实感。”陈墨忘不了那位知名校友言语间的萧瑟之意,“至少每天能做出一些实实在在的东西,能填饱一些人的肚子,还能收获对方的一个笑容。”
陈墨也不认同很多人所说的银行“去能力化”。
在他看来,能力只有不同,没有优劣。他的表哥在一家国有银行总行的党委办公室工作,每次回老家,当地省分行的行长都会到他家拜年。
他感慨,“你能说这种工作不好吗?你能说这种能力不重要吗?”
意识到投行在高薪光鲜之外的另一面后,像陈墨这样果断作出选择、切换道路的人不在少数。
在北大学经济的赵漾曾在一家工作强度和薪资同样出名的投行实习了一年多,最后“身体绷不住了”,胸闷心悸、寻麻疹、肠胃炎全都找上门,断断续续住院一个月。
出院后,她很快提出辞职,一心一意准备银行的招聘。
但她很快发现,另一条路也不好走。银行对于应聘者有着非常明确的偏好——
“硕士,党员,北京人。”赵漾言简意赅。
关于“预期”
徐凯有记日记的习惯。
工作尘埃落定后,他收拾房间,翻出了本科和硕士期间的厚厚三大本日记。
第一本记录了本科第一年和第二年的生活。
他在高考后如愿以偿进入一所排名前列的财经类高校,读金融学。
翻着日记,第一次穿西装拍职业照的兴奋、第一次到证券公司面试前的紧张一一浮现。
本科的第三年和第四年记在第二本。
他曾详细记录和一位在投行工作的学长的“coffee chat”。
对方谈到自己的生活——到全国各地出差如同空中飞人,住高级酒店,吃人均几千的西餐,与身价数亿的企业老板打高尔夫,和国企高层觥筹交错——都令他心驰神往。
看着熟悉的字迹,但字里行间那种带着懵懂的热忱已经远去,徐凯感到恍惚。
随着他考上清华大学的研究生,日记也写到了第三本。
他逐渐见到了金融世界更加真实的一面,比如对优绩主义的推崇。
尤其是进入2023年后,他了解到多家券商研究所开始推行末位淘汰机制,“听到的第一秒会觉得好残酷,但再一想,从这个地方听到好像也很合理。”
找工作的几个月间,徐凯记日记的频率不高,因为忙,也因为“丧”。
他说,就像面对股市,入局的时候每个人都充满信心,但一步步走下来,绝望的情绪顺流而下,一直到底。
2023年11月5日,他整个秋招期间最忙的一天。
从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他面了四家公司,从北京的东边到西北边再到南边,面试之间的时间几乎都在地铁上度过。晚上赶末班车回到宿舍,他筋疲力尽,第二天醒来后记下了这马不停蹄的一日。
最后他写道,“希望有好结果。”
但直到12月初,他仍然一个offer都没有收到。
焦虑等字眼开始频繁出现在日记中。他会随手记下投递的岗位。回头看时,他惊讶自己当时“什么都投”,城商行甚至村镇银行都投过。
笔记本翻到最后一页,只有一句话,是他收到银行录用通知那天写下的。“仔细想想,天天坐飞机、
住酒店,这种生活可能也不是我想要的。”墨迹凝住,又继续,“是不是?”
他也在日记中梳理过一些关于职业的思考。
“一切都是预期的问题。”他写道。
预期,经济学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强调未来的不确定性对于人们的经济行为的决定性影响作用。
当市场环境震荡,从业者的信心受挫,长期预期被重塑。
徐凯的一个同学放弃了一家内资投行的offer,最后考公上岸。
同学解释,他听说了太多降薪、裁员的例子,心有戚戚,“与其说刚进去就被开了,还不如努力进入一个稳定的环境。”
徐凯带着感慨写道,“行情好的时候,大家懵懵懂懂就可以进入鄙视链中位置相对靠上的公司,对未来预期也乐观,觉得年轻的时候累一点就累一点,只要能积累足够多的资本,努力就有意义。
但行情变差,行业偏负面残酷的一面凸显,这时选择进入就需要更大的勇气。”
人人心中都有一个关于职业的“效用函数”,对一份工作的偏好取决于物质回报、稳定程度、成长性、work-life balance(工作生活平衡)等因素。
对于包括徐凯、陈墨在内的很多人来说,高薪、光鲜、富有挑战性和可能性构成了他们曾经对工作的全部想象。
但在逐步感受到行业的寒意后,他们开始主动调低收入和成长性的权重,以换取更稳定、闲暇时光更多的生活。
陈墨庆幸及时调整预期,放弃投行后,他久违地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空闲时间。
他终于可以在周末睡到自然醒,可以每天在夕阳下慢跑,可以和朋友在喜欢的餐厅从从容容地吃完一顿饭,再看个电影。
为了抓住最后的学生时光,他还报名了学校的交换项目,接受采访时正在欧洲游玩。“你看我现在还有功夫出国玩,我要是还做投行的话就得一直实习到毕业。”隔着7000多公里的距离,陈墨轻快的笑声仍然感染力十足。
转换轨道后,同样有人满意,有人彷徨。
对于有朝一日跳出银行体系,徐凯仍然隐隐抱着一丝希望。他觉得,人只要活着,就还可以折腾。“现在行情不好,我选了一个偏体制内的工作,等到未来市场转暖一些,是不是也可以再尝试一下?”
但有时,他悲观地觉得那火光终将熄灭。在银行工作的学长告诉他,很多人刚进银行时都更青睐能发挥和锻炼专业技能的前台岗位,比如金融市场部,但工作几年后,纷纷考虑转岗到中后台部门,如财务会计部、人力资源部。学长开玩笑,“都来银行了,既然这么稳定,不如再‘摆’一点。”
徐凯想,说不准他也会变成一只泡在温水里、不想动弹的青蛙。
前不久的一次校友聚会上,徐凯和同届同学一聊,发现有人回家乡,进国企,有人去了名字都没听过的小私企,他心里挺不是滋味,“虽然刚毕业,但有种一代英雄落幕的感觉。”
在聚会上他还见到了几位在投行工作的学长学姐。“以后就是两个圈子了。”他既羡慕,又隐隐有点别扭,“错开了。”
赞(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