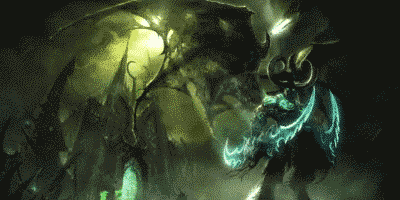Lola|边疆、民族与宗教:国歌不会唱,就不是中国人了
此后,约翰就在贡山、丽江、昆明三地的监狱中度过了31年。
据约翰说,当时贡山监狱关押的人员有六七百人之多,后来人太多关不下,把他们转到丽江,10个人的手臂捆着排成一排,经维西到达丽江。
我生在云南,二十多年来从没离开过这里。印象中也没有觉得这个地方很大,只是用自己常住的地方来衡量,感觉就是群山之间的若干个小地方组成了云南。
中学地理课本上介绍我们,山地约占 84% ,高原、丘陵约占 10%,由此便可以想象,超过 4800 万的云南人就生活在仅占 6% 的河谷与盆地之间。
这里的大部分城市散落分布着,也许飞机是最佳的出行方式。但因为经济跟不上,机场大都设在旅游城市。像我的父母,就至今没有坐过飞机。
上大学之前,我还没有坐过火车,也分不清动车和火车的区别,但是也记得矿泉水瓶身上印的“云南十八怪”之“火车没有汽车快”。我们的主要出行工具就是汽车。
来到腾冲以前,我脑子里自动形成的那张云南地图是完全模糊的,只有从家到昆明的两个点,最多记得经过玉溪。
即便是旅行,也只知道是从一个点降落到另一个点,然后就到了大理、丽江、香格里拉,并不知道它们在地图上如何相连。
腾冲之行让我知道了早已如雷贯耳的“滇西环线”,有一部分是经楚雄、大理、保山,最终抵达腾冲。如果不是因为疫情,也许就可以连接芒市,还有瑞丽。
一路上看着碧绿狭长的怒江之水,于是忍不住想象,顺着这条路往前开,或者顺江而下,又会到哪里。
同行的朋友告诉我,顺着怒江水流淌的方向就能到他家,贡山,最终这条河再流入缅甸。
到这里,滇西环线中我最陌生的几环出现了——但由于高黎贡山阻隔,便不能再继续往前,只能从腾冲原路折返,回到作为交界点的大理,再经由丽江、香格里拉前往剩下的几个城市:德钦、贡山、福贡、泸水。
这就是完整的滇西环线。
我并不熟悉的原因,可能是我至今从未到过怒江——这里的怒江就不再指那条碧绿的流淌在峡谷之间的江河了,而是指怒江州,全称是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中国唯一的傈僳族自治州。
它在地图上和我的家乡所在地,正好处在一条对角线的两端,应该算是离我较远的地方了。
上学时的好友,是住在怒江的白族,她告诉我,在怒江,每一户傈僳族人家的门口都种着一棵野樱花,等到樱花开的时候,班上的同学就开始轮番请假回家,因为当地的风俗是,樱花开到谁家,谁家就过年。
而新认识的一位朋友,则是住在藏区的傈僳族,平时会说藏语和傈僳语。
他告诉我,怒江的藏族会取圣经里的名字,玛丽、玛利亚,他们平时就用藏语喊出这些名字。
但是等到了腾冲以后,又有人向我提起对一山之隔的怒江的印象,就说是城市狭长分布,到处是高山峡谷,非常逼仄、险峻,又时常阴雨连绵,如果不是有很好的朋友在,感觉生活在那里很压抑。
这是我所听到的关于怒江唯一不那么浪漫的印象和回忆,但即便是这样正反两面都有了,我也还是不认识这个地方,常常独自想象它。
有时候感情发生一些错乱,甚至到了怀念的地步,怀念一个我从未到过的地方。
百科词条里介绍,它位于怒江中游,因怒江由北向南纵贯全境而得名,包含泸水市、福贡县、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两个县和两个少数民族自治县 。
这里是中国民族族别成分最多、中国人口较少民族最多的自治州,还生活着人口数量较少的独龙族和怒族。
我对独龙族的印象就是一些照片中文面的老人,她们从少女时代就有文面的习惯,然后戴着那张“面具”,再出现在世人惊叹的目光之前,就已经变成了白发苍苍的老人,好像她们生来如此。
震惊过后也无法探究,那双神秘的眼睛到底在看向哪里。
在怒江州的词条下面,我读到了相关的介绍,最后一行是:“独龙族人相信万物有灵,崇拜自然物,相信有鬼。”
这最后一句,重重地打在我心上,心脏开始咚咚咚地跳个不停,一晚上都让我心神不宁。
好像是一个很短的咒语,让我在一瞬间就连通了这个民族的信仰,不断回想起小时候父母用来警示我们的各种鬼神,以及它们的名字。
云南一共有 25 个边境县,其中怒江州就有三个,包含滇西环线中的三个城市,贡山、福贡、泸水。
福贡第一次出现在公众面前,是丰县“铁链女”的调查结果显示,该女子名为小花梅,就是怒江福贡人,但始终真假难辨,有调查记者到了福贡当地,也无法确认“铁链女”即官方通报中的小花梅。
而泸水则以另一种方式登上热搜榜,傈僳族小伙的一段说唱迅速引起整个互联网的效仿。
贡山,就是我朋友的家乡,他写过一句让我至今印象深刻的话:从怒江,看世界。
写“边疆、民族与宗教”系列第一篇的时候,我正在看一本讲述独龙江一个村子六十年变迁的书,后来我发现,那个村子就位于贡山独龙江乡。
和“怒江”一样,“独龙江”既作为一条江的名字,也作为一个行政区划名称,二者皆可。
在当地,这种情况非常普遍,人们甚至还会按居住地来为自己的家族命名。
村子里的一座教堂被命名为“斯日佐”,也是因为教堂所在地名叫斯日佐,和教堂附近的家族名也一致。
这本书的目录里有一个信息,基督教于 1999 年传入这个独龙族居住的村子,和我的认知有一定偏差。
因为基督徒将整个怒江称为“福音谷”,在传教士傅能仁的时代,基督教就已经在那里开花结果。但我还没读到这部分,就先在一起“边民外逃”的事件中找到了基督教的踪影。
这次“外逃”的主要人群是当地的宗教信徒。作者于 2002 年 1 月 9 日对独龙江的第一代基督教徒约翰进行访问时,约翰讲述了一件关于他自己的、也影响了他一生的事件。
这个事件的影响还不仅仅只是约翰本人,也涉及了很多和他一样有着相同宗教信仰的人。约翰是这样讲述自己的故事的:
1957 年,他被当地基督教会交换到今天位于缅甸境内的木克木冈、库屑一带“教书”半年。
回来后还是住在他原来居住的麻必利(现巴坡村麻必利村民小组),每天打柴五六背。回来后的第三天,他打柴回来,工作队的人来到他家,用枪逼着他,把他押到巴坡关了一夜,第二天被带到贡山县城。
此后,约翰就在贡山、丽江、昆明三地的监狱中度过了 31 年(其中贡山 6 年,丽江 9 年,昆明 16 年)。
据约翰说,1958 年 8 月,贡山监狱关押的人员有六七百人之多。后来贡山监狱人太多关不下,把他们转到丽江,10 个人的手臂捆着排成一排,经维西达到丽江。
1957 年的“约翰被捕”事件,直接导致了 1958 年独龙江巴坡、马库一带的基督教信徒大量逃往缅甸。据当地基督徒迪新生估计,1958 年独龙江逃到缅甸的人大约有两三百人。
这对于当时人口只有 2000 多人的独龙江来说,绝不是一个小数字。
当时中国对包括独龙族生活的地区在内推行“直接过渡”政策,据有关资料:“直接过渡”这一政策,是在 1952 年(云南)省民族工作队到德宏景颇族居住区深入开展工作的基础上,由省边委秘书长马曜到潞西西山进行专题调查后于 1953 年 8 月提出来的。
经省委上报中央批准后于 1954 年最先在德宏地区试行,之后逐步在全省情况相同的少数民族地区推广。
除了云南的八个少数民族(景颇、傈僳、独龙、 怒、德昂、佤、布朗、基诺)之外,还涉及海南的黎族和黑龙江、内蒙等省(区)的鄂伦春和鄂温克族。
据怒江州地方史料记载:1954 年 5 月(云南)省委提出,在阶级分化不明显的景颇、傈僳、独龙、怒、德昂、佤、布朗、基诺族聚居区和部分拉祜、哈尼、瑶族居住的 66 万人口地区,基本不进行内部的土地改革,而是应该以“团结、生产、进步”作为长期的工作方针,在党的领导下,通过人民政府和先进民族长期有效的帮助,创造条件,逐步消除民族的落后因素,通过农业、手工业合作化道路,保证直接地但却是逐步地过渡到社会主义。
在《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大辞典》中仍能找到这项政策的详细说明,百度百科相关词条恐怕也是从这里摘抄的,介绍了“直接过渡”的具体做法,第一条是“宣传党的民族平等团结政策,进行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其他也大都是从中国人民政府工作政绩的角度进行讲述,挑不出什么过错,但始终让人看得云里雾里。
不过结合先前基督徒约翰所遭遇的事,正体现了这一时期居住在此地的民族与当时的新兴国家之间的一种紧张关系,人们对于这样一种社会制度的突变以及声势浩大的社会主义改造,感到无所适从,甚至滋生出了一种恐惧感,以至于这样一种复杂的社会心态最终会化为具体的行动。
在云南的其他边境地区,类似事件也并非罕见。从这些事件中,可以直接感知到当时的政治氛围,以及对于与主流意识形态不相符合的民间信仰的一种彻底的清洗。
注释里还有一份令我感到触目惊心的统计,我也一并放在这里。
据有关资料
1958 年,位于云南南部的沧源佤族自治县外迁人数 14639 人,占全县人口的 21.4%;1954 年 4月 14 日《思茅地委、思茅军分区对今春以来外逃外迁问题的指示》中说,“自年初以来,边疆外逃外迁事件不断继续发生。与往年比,其主要特点是,面更广,规模更大。
截至 3 月底,共外逃 644 户,2433 人。4 月以来,不但没有停止,并有新的发展”;1958 年 4 月 16 日,思茅边防司令部给军区的电报有如下叙述:1958 年以来,我区外逃严重,已达 3000 多人。其中澜沧 1600 人,孟连 998 人,猛混 70 人,猛腊 166 人,江城 10 人。形势仍在发展。
外逃的特点是:
1.普遍性。但澜沧、孟连两区最为严重;
2.由二线以内继续向纵深发展。开始是孟连、糯福区,现在深入到澜沧、孟连内地;
3.外逃人员 65% 是我基本群众,并有骨干积极分子、党团员和政府干部带领,逃跑的地主富农只占少数;
4.整户、整寨携枪结队,公开对抗,不听劝阻;
“大跃进开始以后,外逃人员大量增加。仅西双版纳自治州所属景洪县, 1958 年 9 月到 1959 年初,全县山坝区外流外迁就有 7000 多人,其中,勐龙区就有 6900 多人。1959 年春,贯彻中央的一些松动政策以后,外逃人员大部分回来了。1959 年秋天反右倾,重新实行左的政策以后,边民又大量外逃。
扣除回流人员不计,从 1958 年 9 月到 1960 年 11 月,全县 8 个坝区总计外逃人员 3411 人。
丽江地委和军分区 1958 年 4 月 16 日 22 时《对碧江武装部电话请示要派部队帮助劝阻边民外逃的批示》中透露了以下情况:
1958 年 4 月 15 日晚,碧江县一区联合乡发现外逃 35 人。该县得悉后,于 16 日晨组织 工作队前往该村劝阻,但因路途太远没有追上。在返回中,又遇外逃者 18 人。工作组当即喊话劝阻。对方不听,一直朝工作队方向走来。民兵当即朝天打了两枪。外逃者向民兵射毒箭,伤民兵 1 人。上午9时发生冲突,至下午4时冲突结束。我消耗子弹 200 多发, 打伤对方 7 人,我牺牲 1 人,伤 1 人。
1958 年 12 月 6 日,中共德宏地委《关于少数民族外逃情况的检查报告》中说:从今年 1 月到11 月 20 日止,已外逃 56267 人,占边沿县总人口的 14%。其中傣族和平土改区 27626 人,景颇族直接过渡区 24886 人。
外逃者中,有国家供给干部 189 人,工作干部 62 人,小学教员 46 人,乡干部 75 人,州直机干部 3 人,中央民族语言调查组 3 人。农村党员外逃 181 人,占党员总数的 16.1%。
从逃亡总人数和其中复杂的人员结构来看,也许“约翰被捕”事件只是发生在独龙江“直接过渡”时期的冰山一角。
仅仅是这些数据中不小心露出的一点破绽,就足以让人联想到那个悲痛的纪录片《雪山上的谋杀》,欧洲登山队的摄影师意外录下了中国军队在西藏与尼泊尔边境射杀试图逃离中国的藏民的画面,如影片中的登山客所言,“人们竟因为寻求更好的生活而死”。
但即便有了这段影像,中国政府仍宣称这只是“正常的边境管理”。
而最近 BBC 关于新疆的报道中,黑客披露的文件与《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大辞典》中关于“直接过渡”政策的记载何其相似。
或许也因为有了独龙江在内的几个少数族群聚居地作为历史经验,它已经进化出了一套更完备的应对方案。在一次关于香港危机的记者会上,BBC《广角镜》记者理查德·比尔顿问了中国驻英大使关于新疆营地的问题:“……据我所知这是拘留营,为什么你不告诉我们这些营地的真相?”
这位中国驻英大使的回答是:“首先,我要说没有你描述的所谓劳工营,我们叫它职业培训中心,它们的目的是预防恐怖主义。”
就像它习惯以工作政绩来掩盖“直过区”发生的残酷往事,当无法否认“信徒外逃”、“边民外逃”的事实时,于是就编造有“境外势力”进来(独龙江)“传谣”,“说什么过去在贡山传教的外国人从飞机上运到境外许多物资,吃穿不完,叫怒江的教徒赶快搬到境外去享受。”
这样的话听起来匪夷所思,那些外逃的信徒为什么会轻信这样的“谣言”而不顾艰难险阻长途跋涉要到缅甸去,讲述者却并不细说。
但我们从第一代基督徒约翰讲述自己被捕的亲身经历,就已经可以窥见真相了。约翰被捕后,分别在贡山、丽江、昆明三地的监狱中度过了漫长的 31 年,他所见生灵涂炭,被关押人数竟多到贡山监狱都“关不下”。
他们又做错了什么呢?
恐怕这才是直接导致独龙江的基督教徒大量逃往缅甸的真实原因。
当“直过区”成为历史,2001 年再到独龙江去,会在学校里见到当地的老师在第一堂课上教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作为中国人,就要会唱国歌,其他歌不会唱可以,国歌一定要会唱。
“国歌不会唱,就不是中国人了!”老师虽口口声声说着,却总是把“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歌词唱到《国际歌》的调上去。
(朋友跟我说,从前到怒江去采访的老记者告诉他,高黎贡山上有很多民族今天还会唱国际歌,每个村唱一个声部,问他们,就说是从老一辈传下来的。也许那位当地的老师掌握的国际歌也是自己的祖辈教唱的)
早在 2019 年,新疆集中营的亲历者就描述过一个细节,关押人员每隔一小时就要站起来唱三遍国歌——“国歌不会唱,就不是中国人了!”与这个同样是一竿子插到底,必须要见血的直线思维,毫无意外的吻合。
但只能写到这里了,脑子嗡嗡地想起费子智的那段话,云南是个奇特的案例,它是检证中国文化及政治扩张的整体发展的试金石。
它可以被视为某种模式,如果该模式在政治上是可行的,更进一步的扩张便会随之而来;或者,它可以视为中国兼并原本非汉地区的可能极限之所在。
赞(28)